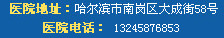唐末,大同军升为方镇,辖云(今山西大同)、朔(今山西朔州)、蔚(今河北蔚县、山西灵丘一带)3州,是为大同镇,这也是本文对“大同镇”概念、范围等的界定。过去,国内的唐史学者以及大同本地学人对大同镇有所讨论。不过,有关大同镇的始置时间、沿革、经济活动等问题,迄今仍存在一定谬误或缺失。本文试依据正史、墓志、地方志等资料对上述问题述之。
一、大同军升为方镇的时间
唐代的大同军,本为河东节度使所辖,其帅称“军使”,管兵约人、马匹,具备一定军事实力。《新唐书》卷50《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在唐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同军使为宿将王忠嗣,其初为河东节度副使、大同军使,后又升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一人领四镇之印,独步天下。
《唐会要》卷78《诸使中》载:“大同军,置在朔州,本大武军。调露二年,裴行俭改为神武军。天授二年,改为平狄军。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改为大武军。开元十二年三月四日,改为大同军。”以上基本书写了大同军的历史脉络。又《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载:“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置。”这时的大同军,约在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盛极而衰,大同军也是这样,领兵人数大为减少。殷宪先生《大同地区出土唐代墓志中的大同城》判定早在贞元六年(),大同军已迁往云州城,之后再未变动。这时的大同军,仍是一个军级单位,约与州同级。大同军是何时升为方镇的呢?相关史籍记载不一,今罗列如下:
1.《资治通鉴》卷“开元十一年()二月”载:“己巳,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按,此为司马光误记,大同军未曾辖10州之地,自然也无开元十一年()二月建大同军节度使之事。
2.《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按,方镇之名有防御、团练、制置,再往上是节镇,称节度使。将“管云、蔚、朔三州”的“大同军防御使”附在至德(-)之后,是为罗列安史之乱后全国广建方镇之概况,不能判定为安史之乱时期已有方镇大同军,这涉及对史料的审读方式、方法。
3.《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载:“会昌三年(),河东节度使罢领云、朔、蔚三州,以云、蔚、朔三州置大同都团练使,治云州。”按,这一记载广为唐史学者采信。
4.《资治通鉴》卷“大中十三年()三月”载:“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胡三省注曰:“时置大同节度,治云州。”按,《资治通鉴》对大同节度的始置时间记载矛盾之处较多,同书又认为“开元十一年()二月”方有大同节度。
5.正德《大同府志》卷1《建置沿革》载:“咸通九年(),置大同军节度。”按,咸通十年()十月,唐中央为褒奖沙陀李国昌镇压庞勋之功,升大同都防御使为大同军节度使,正德《大同府志》将时间定为咸通九年(),不过是误读了史料。
从地缘政治形势看,9世纪40年代初,回鹘内乱,相互争斗不已,回鹘乱军动辄侵犯唐界,唐朝亦多次派兵讨伐回鹘。会昌二年()九月,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对唐朝造成严峻的军事威胁,但此时大同戍兵较少,无法有效防御回鹘。《资治通鉴》卷“会昌二年九月”记载名相李德裕上书称“(孙)俦言不须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换言之,大同此时兵士最多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会昌二年八月”载:“(回鹘)可汗率众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掠河东杂虏牛马数万,转斗至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称张献节为“刺史”而非“防御使”或“团练使”,代表会昌二年()时仍未置大同镇。
大约为经略边地,应对回鹘威胁,同时也为制衡雄镇河东,最终在会昌三年(),唐中央下令升大同军为都团练使,管云、朔、蔚3州之地。从此,大同军正式升格为方镇,在唐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二、大同镇的沿革
会昌三年(),大同建镇,为都团练,领云、蔚、朔3州。
会昌四年(),大同镇由都团练使升为都防御使。《资治通鉴》卷“应顺元年()三月”载:“(杨思权)率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自西门入,以幅纸进潞王曰:‘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勿以为防、团。’”“防”为防御使,“团”为团练使。大将杨思权随潞王李从珂造反,请求将来成功后委任自己为节度使,轻视防御使与团练使,反映了上述官职地位差异之巨。年朔州市应县金城镇城西铺村出土有《唐故云州都防御衙前兵马使曹府君铭志》,志主曹府君曾担任“云州都防御衙前兵马使”,为大同镇高级将领。曹府君“咸通九载,月戴白藏,下旬有八,私第而亡。”据此,至咸通九年()时,大同镇仍为都防御级别,未有变动。
咸通十年(),唐中央以沙陀李国昌镇压庞勋乱卒有大功,将大同镇升为节镇,以李国昌为第一任大同节度使。《资治通鉴》卷“咸通十年十一月”载:“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胡三省注曰:“会昌中,巳置大同军团练使于云州,寻为防御,今升为节镇。”但是,唐中央对沙陀厉行控制、防范政策,大同镇为沙陀繁衍发展基地,如果李国昌担任大同军节度使时间过久,沙陀或许会成为帝国新的威胁。所以,很快,李国昌被派往其它军镇。《资质通鉴》卷“咸通十一年()十二月”载:“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据咸通十一年()《唐故天水郡尹府君合祔墓志》载:尹昶“曾任营田右厢权要,后因府主陇西李公讨伐徐方,选择心手,藉其澣济,特署粮副。”殷宪先生《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认为“府”为大同节度使府,“府主陇西李公”为李国昌。所以,李国昌任大同节度使的时间约为1年左右。
但是李国昌离任大同后,大同节度使再次降为都防御使,时间约在咸通十一年()某月。乾符三年()《李审妻殷氏墓志》载:“令嗣大同军都防御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充清塞军使,曰温让。”李温让在乾符三年()为大同军都防御左押衙,此乃唐末方镇高级军职之一,称“大同军都防御”而非大同军节度,印证了本文上述判断。
乾符五年()初,爆发了著名的“斗鸡台事变”,大同镇将士在李克用的领导下制造兵变,处死大同都防御使府段文楚等5人,事后李克用自命大同防御留后,上书朝廷请求正式委任自己为大同都防御使。段文楚为忠臣段秀实之孙,大同又地处要害,唐中央自然不许这种以下犯上行为,遂拒绝了李克用,计划以其父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安沙陀之心,从而控制大同乱局,防范沙陀势大。《资治通鉴》卷“乾符五年四月”载:“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亦载:“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御使为大同节度使。”换言之,乾符五年()四月,唐中央再次升大同都防御使为大同节度使。然而,五月,“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毀之,杀监军,不受代。”之后,唐中央与沙陀爆发战争,但沙陀数次击溃唐朝联军。无奈之下,次年()夏,唐中央以李克用为大同节度使,以羁縻之。《河洛墓刻拾零》录有《支谟墓志》,载:乾符“六年()夏,任遵谟入奏,固称(李)克用身在,大言于朝,遂除(李克用)蔚、朔、云三州节度使。”为何唐中央如此看重李克用而不是其父李国昌呢?《李克用墓志》给了答案:“以统军(李国昌)请老,表王(李克用)代将部族。”不过,这个时候云州城为吐浑赫连铎所据,李克用虽名为大同节度使,其实控制的地盘不过朔州城、蔚州城以及其它小的县城或戍栅。
广明元年(),唐中央与沙陀再次交战。但沙陀寡不敌众,国昌与克用领族人亡达靼。《资治通鉴》卷“广明元年七月”载:“诏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亦即这时的大同军仍是都防御使级别,不是节镇。黄巢起义军攻陷京师后,唐中央恕沙陀之罪,重新启用李国昌父子,以李克用为雁门节度留后。《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载:“中和二年(),以忻、代二州隶雁门节度,更大同节度为雁门节度,领左神策军,天宁镇遏观察使,徙治代州。”事实上,大同镇仍为都防御使,不是节度使,也不存在以雁门节度代之,徙代州事。此时,唐中央给李克用划定的活动范围仍主要是忻、代2州,不包括云州。
中和三年(),李克用复京师,功第一,官拜河东节度使。
中和四年()八月,云蔚防御使废,州隶河东。《资治通鉴》卷“中和四年八月”载:“(李)克用奏罢云蔚防御使,依旧隶河东,从之。”《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亦载:“河东节度复领云、蔚二州。”唐中央采取姑息之策,名义上云州改属河东,其实仍为赫连铎所据。
大顺二年()七月,李克用逐赫连铎,攻下云州城,以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资治通鉴》卷“大顺二年七月”载:“李克用急攻云州,赫连铎食尽,奔吐谷浑部,既而归于幽州。克用表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
大约乾宁元年(),大同防御使已废。《资治通鉴》卷“乾宁元年九月”载:“(李)克用表云州刺史薛志诚(“诚”为“勤”之讹)为昭义留后。”此时,薛志勤主政云州,但其官名已为云州刺史,而非云州防御使或大同防御使。大约李克用为经略大后方,所以将云、朔、蔚3州由自己担任的河东节度使管辖。殷宪先生《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录有天复元年()《石善达墓志》,其志文很大程度上能佐证本文上述判断。《石善达墓志》全名《□大唐北京太原府朔州兴唐军石府君墓志》,从墓志名来看,北京、太原府代称河东节度,朔州为其所辖,兴唐军又为朔州所辖。亦即天复元年()时,本为大同防御使管辖的朔州隶河东节度使,从侧面反映了此时大同防御使不存。之后迄唐亡,大约再未有大同防御使之置。
三、大同镇的经济活动
唐末大同镇生活的人民有多少呢?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朔州开元户,元和户;蔚州开元户,元和户;云州开元户,元和户阙载。据此,大同镇所辖云、朔、蔚3州编户约1万多人。这自然不是大同镇全部居民,还有士兵与杂虏未被计入。大同镇主要由游牧民族构成,还有一定数量戍守城栅的士兵。其中唐末大同镇生活的游牧民族大约有突厥、回鹘、沙陀、吐浑、昭武九姓、契苾、达靼、奚等。游牧民族与中原人士外貌、体型、语言多不相同,例如,沙陀人多“深目虬须”。此外,突厥人张彦泽,《旧五代史》本传记其“目睛黄而夜有光色,顾视若鸷兽焉。”乾符五年()“斗鸡台事变”之初,李克用有兵近万人。《唐末三朝见闻录》载:乾符五年()二月四日,“两面马步五万余人,城四面下营。五日,又赏土团牛酒。六日,监军使送版印与李九郎。”“李九郎”为李克用,“监军使送版印与李九郎”,代表大同镇将士服从李克用。“马步五万余人”,似乎大同镇在乾符五年()士兵最少在5万以上,这是不合理的,疑“马步五万余人”之“五”为衍字。《资治通鉴》卷“广明元年()”载:“二月庚戌,沙陀两万余人逼晋阳。……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来降。……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大破之,杀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据此,大同镇效忠李克用的兵力有2-3万人,以戎狄居多。综上,本文初步预测此时大同镇总人数有10多万人。
唐末大同镇云、朔、蔚3州的贡赋是怎样的呢?《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云州土贡有犛牛尾、雕羽,朔州土贡有白雕羽、豹尾、甘草,蔚州土贡有熊鞹、豹尾、松实。《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载:云州,开元贡:雕翎五具。赋:布、麻。朔州,开元贡:白雕翎四具。蔚州,开元贡:熊皮、豹皮。赋:麻、布。《通典》卷六《赋税下》载:蔚州,贡松子一石。
虽然部分游牧民族也担负戍边之责,如沙陀等,但唐末的大同镇无疑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唐末全国气温有所下降,对地处塞外的大同镇而言,大范围发展农业存在较多问题,或许此时也有部分军事性质的农业活动,但想必大同镇粮食不能自给,所以由水陆发运使负责粮食等军用物质的调派。乾符年间,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身兼代北水陆发运使一职。《资治通鉴》卷“乾符五年()正月”载:“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本文认为,段文楚负责以漕运或陆路的方式转运粮食等物资。《全唐文》卷录有《薛謇神道碑》,薛謇“局居雁门,主谷籴,具舟楫……每发粟溯河北行,涉戎落,以馈缘边诸军及乘障者。”“雁门”郡,即代州。由代州发运粮食溯河北上,运往云、朔、蔚等州戎族居地,来为戍边士兵补给。
殷宪先生《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录有光化三年()《赵礼墓志》,全名为《唐故河东节度衙前兵马使知云州别贮仓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天水赵府君墓志》。志文载:“(赵礼)署节度贮仓官,受纳诸州赋税,计其耗羡。不□□于民,一年而阜集山堆,二载而千箱万庾。加以管内有未踵于穷秋、不计于朝夕者,□君咸施沾拯,悉赖赈矜。”从赵礼的官职河东节度衙前兵马使、知云州别贮仓务来看,其应为沙陀李晋王财政官之一。“受纳诸州赋税”,代表赵礼管辖范围不止云州,还有其它州,大约有朔、蔚等附近州县。最后的结果是“一年而阜集山堆,二载而千箱万庾”,敛财如此之快,又反映了李克用为稳定后方,在云、朔、蔚等州县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建设,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不过,志文对墓主赵礼有过誉之嫌疑,在战争态势下,不宜对云、朔、蔚3州的经济形势有过好的预计。
四、余话
唐末大同镇几次地位的升降变迁,与沙陀李国昌父子有很大的关联。9世纪40年代初,回鹘内乱,李国昌(其时名“朱邪赤心”)领沙陀部参与了针对回鹘的多次军事攻击。为防御回鹘乱军、经略边地、压制雄镇河东,会昌三年(),唐中央决定将大同军升为方镇,是为大同都团练使。次年(),再升大同都防御使。咸通十年(),李国昌的沙陀军在攻残庞勋起义军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奖励其功以激励将士,唐中央升大同军为节镇,李国昌为第一任大同军节度使。但是很快李国昌被移往它镇,大同节镇复降级为都防御。乾符五年()初,李克用制造“斗鸡台事变”。为稳定边塞,唐中央决定再次建大同节镇,调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军节度使,但为李国昌父子拒命。次年()夏,为争取缓冲时机,唐中央无奈之下以李克用为大同节度使。等广明元年()李克用被击溃后,唐中央以赫连铎为大同都防御使,大同节镇再次降为都防御。
后晋天福年间,大同镇为辽所有。一百多年之后,地缘政治形势再次有了新的变化,大同镇正好处在辽与北宋、西夏版图交界处。在三方鼎立局面的影响下,重熙十三年(年),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大同将再次迎来自己灿烂的历史时刻。
来源:文史艺苑
发布:中国经贸融媒体中心
责编:明德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l/8772.html